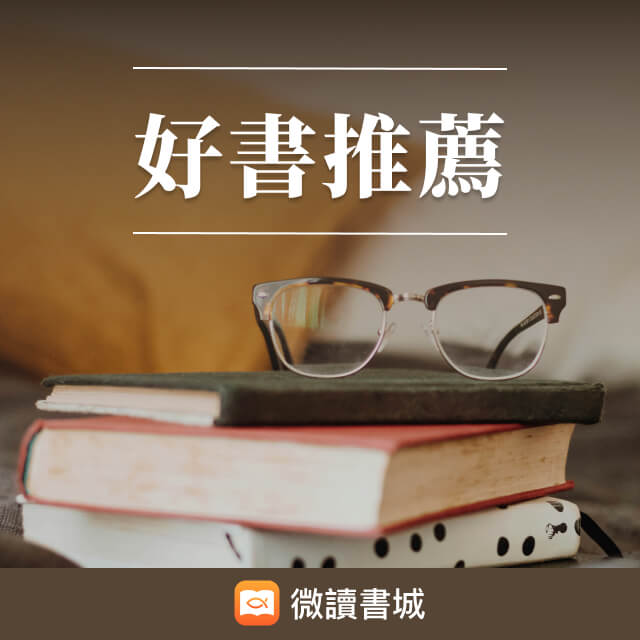“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讀《神的中保:祭司職事的聖經神學》
作者:伊薩
祭司職事是個很重要的主題,它“不僅貫穿兩約,也是聖經神學的主要軌跡,沒有這個主題我們就很難理解耶穌基督的使命、生、死、復活及其持續中的崇高事工。”(叢書前言,卡森)然而,儘管對祭司職事的研究有很多,但在此之前,基於聖經正典的祭司職事研究似乎沒有達至書籍規模的。安德烈.S.馬龍(Andrew S. Malone)的著作《神的中保:祭司職事的聖經神學》(God’s Mediators: A Biblical Theology of Priesthood)是D.A.卡森(D.A.Carson)主編的“新聖經神學研究”(New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系列作品之一,它的問世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馬龍是澳大利亞墨爾本里德利學院(Ridley College)的聖經研究講師。他的跨教派經歷使得他在研究祭司職事等主題時,能夠從不同的教會傳統中汲取靈感,形成獨特的神學視角。本書結構清晰,重點突出,共八章,分為兩大部分。作者在第1章對自己研究祭司主題的緣起,以及對聖經神學的認識和基本方法作了介紹,為後面的內容作鋪墊。第一部分(2-5章)聚焦於神的個體祭司,第二部分(6-8章)則專注於神的羣體祭司,並在第8章結合當今基督教會的情況對此主題作反思性總結。
馬龍用掛毯的概念來描繪聖經神學:“系統神學更傾向於在一個特定主題上辨別出一次性的觀點……聖經神學則對整幅掛毯在編織過程中所產生的複雜變化保持警覺。”(第1章)為此,他帶領讀者追溯聖經對祭司職事的逐步揭示,就像一步一步地觀看一幅畫像完成的進程,主要觀察經文掛毯上的兩條主線:一條是個體祭司,一條是羣體祭司。
出人意料的是,馬龍從出埃及記而非創世記來談論祭司職事的聖經神學。但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祭司制度是從西奈山開始建立的,並且會幕的建造及人事安排,獻祭的條例等都是在以色列人停留西奈山期間發生和頒佈的。為此,我們看到這兩條主線都是從出埃及記19章出發,接着倒敘回創世記,然後再回到民數記10章之後章節和書卷,最後來到新約。順着舊約到新約的書卷順序來追蹤祭司職事這個主題,不僅因為這是聖經神學的基本線路,更是平行對照的需要。個體祭司的連貫性和非連貫性讓我們看到人類祭司的有限和大祭司耶穌基督的超越和完美,羣體祭司的一致性和變化讓我們更深明白神對祂子民不變的呼召,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這個時代活出呼召,作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民。
祭司的出現是爲了緩解上帝與以色列關係上的張力,這個張力主要是因為神的聖潔和人的罪。馬龍對三類會幕人事(大祭司,其他祭司以及他們的助手利未人)作了詳細分析,指出祭司的中保作用是縮小神與人之間的鴻溝,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在百姓面前代表神,其主要工作是“和解”。為達此目的,祭司自身的聖潔極其重要,大祭司的聖潔級別最高,因為他離神最近。大祭司擁有特殊的位分連帶重大的責任,他的死標誌着一個歷史時代的結束,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除了亞倫之外,作者還考察了三個重要的個體祭司或祭司式人物:1)摩西。摩西雖非亞倫制式的祭司,但實際上有許多中保活動是與亞倫和他的繼承人一同執行的,他甚至比大祭司與神更親近。因此有學者認為摩西的祭司式行為可能和他君王式的位分有關係。2)亞當。作者指出伊甸園的結構、目的及使命並非與以後以色列敬拜的模式毫不相干,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的工作具有祭司甚至君王性質。神要在以色列中間行走(參利26:11-12),與祂在伊甸園中“行走”尋找亞當夏娃(創3:8)之間存在神學對應。3)麥基洗德。他既是撒冷王,又是祭司。作者認為,“這些早期祭司很少和君王角色分立。”(第3章)
作者對歷史書的梳理讓我們看到以色列祭司的發展軌跡:1)從撒母耳開始,先知在以色列的領袖角色如旭日初昇,祭司職事制度似乎退居二線了。2)大衛家的君王雖不是祭司卻擁有祭司的職能,也就是說,當以色列正式引入王權時,我們發現祭司與君王職事的重疊。3)以斯拉引介並且示範了一個新的階級“文士”,他們擁有“祭司文士”的名號,接替了祭司的教導職分。舊約祭司中不乏忠心之人,也有嚴重失職者。以色列人的被擄與祭司的失敗密切相關,儘管如此,神有意復興此職。
第5章對希伯來書的討論將第一部分推向了高潮。希伯來書向我們描述了完美大祭司的關鍵特徵:“一方面,聖子在永恆如一的順服之中與父上帝有不可動搖的連結;另一方面,聖子在永恆如一的憐憫和理解之中與他的人間弟兄有不可動搖的連結。”祂真正實現了中保的角色,是名副其實的pontifex(拉丁語“祭司”的意思,語源學的解釋是“建設橋樑的人”),並且祂在天上聖所裏的祭司職任長久不更換。相比而言,啟示錄對耶穌祭司職事的描述有些一閃而過和隱約。
馬龍在第6章轉向另一條主線“神的羣體祭司”,也從出埃及記第19章開始梳理。神呼召以色列歸祂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賦予以色列獨特的位分,將他們擡舉到各民族之上。作者在出19:5-6與創世記12:1-3的結構上尋找平行,表示神揀選亞伯拉罕從而揀選以色列,目的是為祂賜福萬國的救恩計劃服務的。因此,這個呼召其實賦予了以色列宣教的使命,正如所羅門在禱告中所說,“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樣(王上8:43)。”
第7章向我們顯示了這種羣體祭司職事在新約之下的面貌。彼前2:9的措詞顯然是從出19:5-6來的,它將舊約子民相同的位分和角色賦予了新約子民。啟示錄有3段經文(啟1:5-6,5:9-10,20:6)都提到信徒要成為國民,歸與神作祭司。這些措辭表明,神對於他舊約子民的應許及期望,延伸至不分背景的基督信徒。啟示錄22章更引進了君王的措詞,敬拜神的人將“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作者贊成“教會兼有羣體君王祭司雙重角色”的觀點,這解釋了為什麼舊約將祭司的權力賦予大衛和所羅門等君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作者在第一部分的討論突出君王和祭司的重疊。
顯然,這兩條主線並不是完全平行而是交會相融的。在舊約,個體祭司是從一個羣體內選拔出來的,與此同時,神委任全體以色列民為一個羣體性、全國性的祭司職事。新約將個體祭司的概念轉移、甚至轉化到耶穌身上,又將以色列國民的祭司羣體責任轉移到囊括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神的教會身上。但這不是簡單的轉移而是轉化。在新約,信徒祭司的觀念是從耶穌個人的祭司職事衍生而來的。作者感嘆,由於語言學及神學語源學的問題,由於千千萬萬讀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會傳統,今天我們很難有一個與聖經所描繪的配合無間的“祭司”觀念。“雖然所有信徒皆祭司,但是所有信徒都不是(專職)服侍人員。”(8章)
馬龍的《神的中保》細緻而深刻地探討了祭司職事的發展脈絡,為此,作者做了大量專注而又細膩的釋經工作。他強調,新舊約中的羣體祭司更具延續性,羣體祭司的宣教使命仍是今日信徒的義務與責任。這激勵今日信徒思考:我們如何在教會生活中、在世界中活出羣體祭司的身份?願我們都信靠主,效法保羅做神福音的祭司,在至高的大祭司耶穌基督裏面被建造成為聖潔的祭司,獻上討神喜悅的屬靈祭。